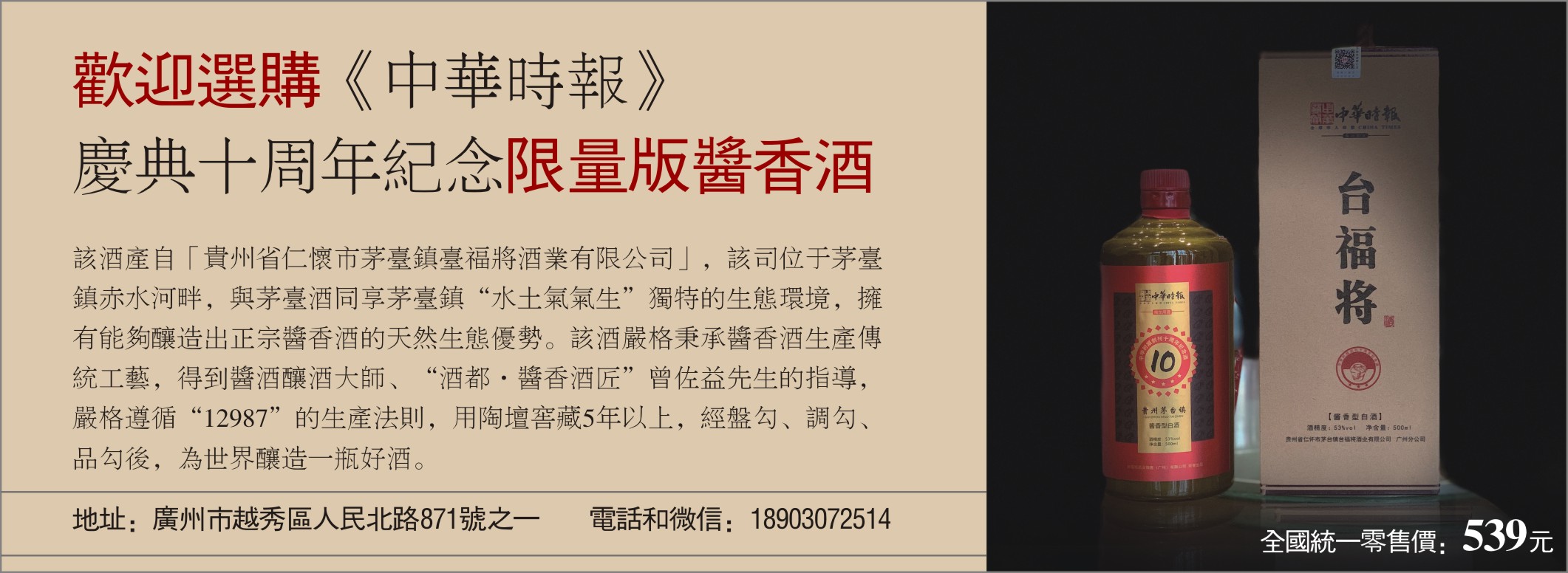- “气墨”“灵象”是新概念、新命题
- “气墨”是墨的未来,“灵象”是象的远方,非常美妙
- “气墨灵象”是至高的审美追求
- “气墨”“灵象”一体且互为形式内容,很有意义
新的审美范畴 新的艺术命题
《“气墨灵象”艺术论》学术研讨会发言
李晓柱

李晓柱
关于“气墨灵象”,前两年,应该是跟吕国英先生在一起,听他介绍过。但是对这个过去一直没有过、也没有听说过的特殊词汇比较模糊。因为没经过深入思考,我就粗浅、判断,以我自己的理解,去表达一下我自己对这个新的审美范畴、新的艺术命题怎么看,尤其作为一个实践者,谈谈我自己的没有经过认真研究与思考后的看法。
我是画中国画的,其实对传统中国一些笔法、墨法,了解并不是太多。“气墨”这个词,因为没有过,是个新的概念、新命题,我当时就觉得有点陌生感。原来我们一般都讲气韵,这些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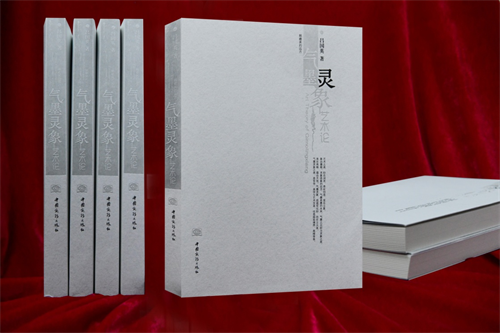
吕国英 著《“气墨灵象”艺术论》
后来我简单粗浅的看了一下,其实“气墨”可能更多有一种墨的幻化、无穷内在的东西。所以说其实他生命运行,跟与生命演化,其实是互相关联的。我觉得他说的“气墨”,实际上“墨”在表达象境的生发,也就是有无限的可能。而且气是动因,“气墨”我就理解到这。
“灵象”这个词我比较感兴趣,我在绘画一直做努力,所以我对“灵象”这个词比较感兴趣的。因为我觉得“灵象”,其实是一个心灵的世界,是人心笼罩的“象”。这个“象”是外部一体,互相关联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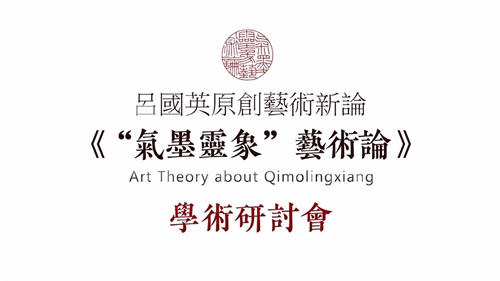
《“气墨灵象”艺术论》学术研讨会(LOGO)
这个“象”获得它的方式,主要就是内观,好多人其实都有,所有灵性都有。所以我觉得一个是靠内观获得,再一个靠灵悟,感性的、直觉的获得“灵象”。反正我是这么认为。其实“灵象”,是由内心观照的世界,也可以说内心创造的世界。这个“灵象”跟我们现在所有流行,就在当下我们对有限的时空无限探研与感知,可能有关系。我们说原来认知到,我们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在我们心灵深处又是什么样的。现在科学证实地球以外,包括量子所有物理性发现,其实都是在我们认知之上东西。
这些来讲,对中国人来讲,可能就是灵性的存在。所以说这个“象”,也许是世界最真实的东西,不像我们眼睛看到世界的样子。所以我觉得“灵象”这个词,提的也特别好,而且我是特别喜欢。我觉得“灵象”应该存在于,应该是我们内心这种反观,应该能看到。而且可能是一个站在高维看低维,看三维世界,能感知到的东西。“气墨”和“灵象”一开始我理解,一个是法一个是道,“气墨”其实为了表达“灵象”为了承载这个道。但是“气墨”和“灵象”本身,二者又是一体,而且又可以互相纠缠,还能互相反转。所以我觉得“气墨灵象”这个理论,词合不合适先放一边,最起码这两个东西是一体的东西,气和道,完全存在于这4个字之内的一种东西,所以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

《“气墨灵象”艺术论》学术研讨会现场
我这里有两个东西,我比较有兴趣。“如气化墨,载灵承象”,实际上就是说墨的动因就是气,我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同时“气”,可能是我们一种心灵的气,也许是其他的无心的一种东西,使墨发生了幻化,用它来表达无尽的“象”。 书中说,“气墨”是“墨”的未来,“灵象”是“象”的远方,真是很妙。我觉得“墨”作为艺术创作的重要元素,通过艺术家之运化,在与诸创作元素多次“天人合一”“天我为一”的化妙中,和融于创作境界,进入精神高维,呈现审美状貌,矗立大美生命之存境。就艺术立象从具象、意象、抽象、“三象合一”之演进而言,相对应的“墨”从经历了线墨、意墨、泼墨、朴墨,最终将走向“气墨”。关于“灵象”是“象”的远方,我觉得是一种很高甚至是至高的追求。现在好多艺术创作,以我们人物画领域来讲,大部分其实就没有深入到精神层面,大部分是在可以说是形象阶段,并没有真正进入一个对现实反观状态,基本上没有,基本上在现实里寻找社会化生动性、担当和责任。基于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上升更高灵魂层面,去对现象进行审美解读。
所以说现在存在的问题,其实很大的。理论对于艺术实践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这个理论——《“气墨灵象”艺术论》的提出,让我们其实面对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可能我们好多人就会把自己的视野放宽,不仅仅局限于我们所认知的世界理解问题,也许站在更高维层面或者通过自己的修行,可能反观我们面对的世界,反观我们内心的时候,获得不同的答案。所以我觉得“灵象”的世界,可能就是我们的希望能看到的世界,而且是我们确实的一个真实的世界。

《“气墨灵象”艺术论》学术研讨会部分专家合影留念
其实大家都在寻找真善美。有的时候到底什么是真,其实自己搞不清楚。因为我们认知,也不可能寻找到真正的“真”,只能达到艺术的“真”。艺术能解决无限性,能解决心灵和寄托。科学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科学只能解决生存问题。所以有这样一个新理论——《“气墨灵象”艺术论》的提出,可能对我们艺术的发展,会有特别大的好处和深度,希望吕国英先生的大作,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_5e95435ff2aac-243x3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