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似乎击穿了中国社会的心理底线。“铁链女们”的悲惨命运引发了山呼海啸般的民意,也映射出政府权力的麻木不仁、昏聩,以及腐败。在民意的推动下,政府被迫针对被拐妇女推出调查和治理措施。在中国各级政府的公信力在铁链女事件中消失殆尽的背景下,我们来探讨一下中国拐卖妇女现象屡禁不止的深层原因以及可能的解决路径。
姚诚2011年冬天在安徽省大别山一间柴房里见到了19岁的被拐卖妇女邓露荣。作为退伍军人的姚诚当时在参与人权组织“中国妇权”解救被拐妇女儿童的行动。
因为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引起的有关妇女拐卖的持续舆论风潮,姚诚在二月中旬首次通过Youtube的视频平台,回忆了这一经历。
中国退伍军人姚诚(视频截图)
一次并不成功的解救
“她躲在柴火堆里,抱着她双目失明的儿子,问她什么话,她都不说,很麻木,”姚诚回忆说。
邓露荣回答解救者提出的问题时,时而清楚、时而模糊。姚诚介绍说,他们当时判断邓露荣患有轻微的智障。
本台记者从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妇权”组织核实了邓露荣的部分信息。邓露荣家住安徽省宿松县柳林乡,因为是超生,被父亲弃养,13岁时被村里的乡村教师强奸,14岁时被叔叔卖给了附近北浴乡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邓露荣的丈夫,也不应叫丈夫,因为并没有结婚,就让她在村子里接客,村子里从六十岁到三十岁,以及更小的找不到老婆的男人跟她睡觉,一次收20元钱,”姚诚介绍说,这个男人用她卖淫的钱盖起了小楼。
“中国妇权”团队的人前去探望邓露荣,直到第三次才见到她,因为很多时候邓露荣并不在家里。姚诚说:“村子里的人说她受不了,受不了这么多男人的虐待,她跑了,经常跑。她跑到山里面去,睡在草堆里,在地里扒着庄稼吃,典型的一个现代白毛女。”
但邓露荣还是要回去,姚诚说,她这么做是为了看自己的儿子,还在襁褓中的儿子因为眼睛发炎,已经双目失明。
姚诚和同伴们解救邓露荣的这次行动并没有成功。当姚诚还在柴房里询问邓露荣情况时,他已经感觉到迫近的危险,“我们发现很危险,门口围了很多人,拿着扁担和锄头过来,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想把这个事情揭露出来,如果这个事情揭露出来,这些男人是犯罪。”
团队被迫离开后,去当地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却以“私了”推脱,不愿插手。如今,十一年时间过去了,“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今年2月24日在推特上说,当地公安不作为,邓露荣至今“饱受煎熬”。
“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张菁提供)
那一个个黑暗的角落
张菁所领导的“中国妇权”虽然在被拐受害人的家属面前是拯救者的形象,但她告诉本台,当她面对一个个被拐卖妇女的个案时,心情常常是崩溃的,“有时候我们救不到人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象邓露荣的这个案子,我们找到她,帮她报警,都做了这么多,可还是救不了她。”
“中国妇权”于2007年成立中国妇女儿童保护中心,开始着手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行动。姚诚也是从那一年加入这一工作,他介绍说,这一行动的参与者一开始就约定以志愿者的形式加入,自己贴时间贴钱。
姚诚告诉本台,他负责的主要是解救被拐儿童的工作,儿童中大部分是女孩,“这些儿童被拐卖以后,就像丰县铁链女一样的,被拐的时候是儿童,后来长大以后,然后需要寻亲。所以我们找儿童的时候,一半以上找到的都是妇女,就是成家生孩子以后的妇女。”
从中国法院历年公布的相关案例看,妇女被拐卖的方式多种多样,有暴力抢人、下迷药、诱骗等等,一般都是在违背被害人意志的前提下进行的。出于对妇女拐卖现象普遍性的担忧,有网友无赖地调侃说,在你和铁链女之间只有一闷棍的距离。
姚诚分析说,女孩子被拐卖后的用途比男孩子要多得多,“买一个女孩子,几千块钱,养在家里当一个劳动力,养大了以后做儿媳妇,省钱啊。还有一些人贩子看重女孩子的经济效应,就把她们送到娱乐场所,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多了。”
姚诚的说法实际指出了被拐卖妇女和女孩的主要出路,包括强迫婚姻,强迫劳动和所谓娱乐场所。也有少数地方,包括山西、湖南等地,曾先后爆出有被拐卖妇女被卖尸配阴婚。而娱乐场所大部分指的实际是色情行业。
中国艾滋病权益活动人士万延海90年代在中国政府的卫生部门任职期间,曾在中国性工作者中推行卫生安全措施。在实际工作中,他观察到,有不少的女性性工作者很可能是被拐骗的,“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就是被家乡那些所谓成功的大姐带出来的,到了都市里才发现原来是做这个,有的人会一直反抗,有的人会被强迫,但有的人可能也就接受了,这些情况都蛮多的。”
万延海向本台坦言,因为主要从事卫生安全的工作,即使发现了有被拐卖人口,也不方便向警方举报,因为这样无法取得娱乐场所老板的信任,工作就没法继续了。
中国艾滋病权益活动人士万延海(视频截图)
“三百多万被拐儿童大多数是女孩子”
从全中国范围看,被拐卖女性(包括成年妇女和未成年女孩)的数量很难获得准确的数据。纽约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郑恬恬2018年在英文学术期刊《历史考古学及人类学期刊》(Journal of Historical Archaeology &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上发表文章,综合国际组织的调查数据统计得知,从2000年到2013年,中国被拐卖的青年女子和小孩总数为92851人。但她强调,实际的被拐卖人口可能要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姚诚依据他多年从事解救被拐儿童的经验,给出了一个估计,“从1980年一直到2016年放开二胎,最高峰的时候,一年就有二十万孩子被拐。我们自己统计,平均每年有十万个孩子被拐,一年十万,十年一百万,三十多年就三百多万。”
姚诚前面提到被拐儿童中大多数是女孩子,这种估计也符合世界的一般规律。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6年发表的报告称,在2014年获得的71个国家数据中被拐人口有96%是女性。
实际上,很多被拐受害人的身份难以确认,因而难以被统计。姚诚介绍说,“很多孩子找不到是因为被洗白了,就是买孩子的家庭花点钱给派出所那些户籍警,给她们上了户口,上了户口就没法找了。他说是他家人,有户口,编了一个出生日期、名字等等,你没办法找了。”
江苏徐州铁链女的真实身份至今成谜,虽然江苏省政府的第五份通报认定她就是结婚登记照上的杨某侠,也就是云南的小花梅,但网络舆论对她的真实身份仍有广泛的质疑。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拐卖人口数据的统计似乎讳莫如深。美国国务院2021年发布报告称,这已经是连续第四年中国政府没有公布人口拐卖受害者的任何数据,这可能与中国政府在一些地区执行强迫劳役,并大规模拘禁维吾尔族等少数族裔的做法有关。
跑不掉的被拐妇女
被拐女性的流出和流入在地域分布上有大致的规律。纽约州立大学的郑恬恬在前述文章中提到,卖出地比较集中的地方包括安徽、贵州、河南、四川和云南等省,买入地则包括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和内蒙古等省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
被拐女性就像商品一样被人贩子售卖。据中国官媒《检察日报》报道,离铁链女事发之地不远的徐州市姜集村早在2000年就是苏北最大的“人口批发市场”。
目前这些女子在“市场”上的价格与过去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姚诚指出,在90年代中期之前,男孩和女孩的买价差别巨大,“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男孩子要一万多,女孩子一千元;但在1995、96年之后,就都达到两三万了。”
郑恬恬2018年的研究则指出,买卖一名被拐女性的价格从6000元人民币到40000元之间。
在被拐卖的女性中,存在大量被虐待、被强奸或被性奴的现象。她们常常困在这样的处境中十年、二十年,无法逃脱。
从云南被拐卖到安徽的妇女董茹(应受访者要求化名)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提到她同村的一名女子被拐卖到安徽,遭买家虐待致死的事情,“我一去看她婆婆就骂,我就叫朋友去看。我朋友跟我说,她整个人都废掉了,被一家人打骂到她傻掉了,一家人又硬把她饿死。”
张菁则告诉本台,被拐妇女如果遭虐待,并被常年禁锢,大概率会造成她们精神失常,“这人哪,人的情绪常年紧张而愤怒。她们还常年没人说话,一个人独居,还要遭受身体上、心灵上的创伤和虐待,所以不疯都要疯。”
在有的情况下,被拐妇女被买家禁锢,会产生畸形的依赖心理。张菁说,当时他们的团队就评估本文开头提及的邓露荣可能有斯德哥尔摩症,离不开那个“家庭”。
“长期被虐待的人,当她们觉得这些已经成了习惯,成了生活一部分的时候,她们可能就会没有意识说这是虐待,反而会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然后,哪天给她一点好处,给她一件衣服穿,给她一点好吃的,她就感恩戴德的。”
也有些人会自始至终地坚决反抗。2007年以真实人物为原型拍摄,反映被拐妇女命运的电影《盲山》主人公白雪梅是一个女大学生,被拐卖到山区,多年后,当她的父亲和警察找到她并试图解救她时,却受到村民阻挠。白雪梅情急之中,一刀砍向了所谓的“丈夫”。这样的艺术人物在现实中并不难找到更多相似的案例。
还有一些被拐妇女在被解救后,却选择回到收买家庭。姚诚和张菁共同提到2009年他们在福建解救的贵州女子肖光艳。7岁就被拐卖变成童养媳的肖光艳,在25年后寻亲终于找到原生家庭,但之后还是回到了福建的夫家。类似的案例在福建还有好几起。
张菁解释说,“因为她们觉得就在这里长大了,这里还是好。反正哪里都有受苦的,他们也有对我们好的时候。”
吊诡之处在于,当被拐女性以身不由己的方式被裹挟进了一个她们未曾预料的命运分岔口之后,她们所遭遇的也未必是地狱。
中国著名辩手、哈佛大学法学博士詹青云近日在接受网络博客“不合时宜”的采访时说,她有一位表姨妈年轻的时候被拐卖到江苏农村,但二十年后寻亲找回家乡贵州,但她是象探亲一样回来的,她对被拐卖以后的生活感到满意,因为江苏的生活比贵州要好,收买的家庭对她也不错。
反映被拐妇女命运的电影《盲山》剧照(百度百科截图)
溃败的农村 放任的权力
在种种被揭露的拐卖妇女的案例中,乡村往往呈现出麻木、冷漠的面目。一根长长的锁链套着江苏徐州铁链女的脖子那么多年,一个硕大的铁笼关着陕西佳县铁笼女那么多年,周围的村民似乎都不闻不问。
村民有时甚至是帮凶。在姚诚想要解救而不成的邓露荣周围,环伺着随时想要扑上来,不让人带走她的本地几十号男人。
这样的村庄里似乎没有法治,警察不执法,面对这些被拐卖妇女的哀告和求助,国家公权力竟然完全缺位。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在2月初就此发表文章,重提她2007年分析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时的一个论断:被权力和治理放任和抛弃的社会底层,其生态将迅速恶化。
中国一位曾参与过打击拐卖行动的资深警员匿名向本台分析说,在铁链女事件中,当地的公安机关存在严重失职,“首先当地警方足以能够发现(这种事),公安部搞的包村制度,每个村都有包村警察,每个乡都有派出所。普通的一个乡管十几、二十个村,多的也就三十个村,那怎么能发现不了呢?”
他说,这个事件中失职的不仅仅是警察,还有基层政府、村委会的领导,但公安机关应该承担首要责任。但他也强调,农村地区基层派出所警力严重不足,工作压力也大,“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所有工作都在基层,就是各种活。上面说不让基层警力参与非警务活动,但实际上基层公安机关太多的非警务活动了,这几年的上访稳控等等压力太大。”
这位警员进一步分析说,重要的是打击拐卖并没有被纳入警员的考核体系,“打拐不考核啊,上面重点考核的内容中没有打击拐卖这一项。上面不重视,我们工作也忙,警力很少,谁去管这种事情啊?”
安徽被拐卖女子董茹告诉本台,她被丈夫虐打时,就发现报警没用,“特别是像我老公他弟弟他有能力,跟村干部(关系)好,我就是去警察局我也搞不过他。再一个就是政府,你不了解,没有用地,警察局也不讲道理,不会向着你一个外地人的。”
在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对拐卖案件的办理也受制于地方保护主义。姚诚介绍说,他们一旦发现被拐儿童的地点,只能去找派出所解救,因为他们没有执法权,但派出所大多不愿出力,“我们到村子里去解救孩子的时候很危险,经常被打出来,因为他们买一个孩子也花了钱,你把他孩子弄走,他要跟你拼命的。所以解救方面只能靠政府,但大部分的时候,政府有地方保护主义。”
北京大学刑法学教授车浩二月初在学术期刊《中国法律评论》上发表文章指出,“面对有刚需性的买媳妇的农民,指望与这些人历史地、文化地共同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办案人员去下狠手从重打击,那也只能是一个美好的理想。”
他强调,买方可能就是当地熟人社会网络中的一员,办案人员并没有强烈的正义动机去认定买方的强奸、拘禁等重罪,往往是按照收买行为的轻刑去处理了,而且往往是搞个缓刑。
一名被拐卖的妇女(法新社图片)
政府里的拐卖利益链
但这些本该看顾社会底层的公权力似乎并不仅仅是抛弃了底层的人们。姚诚和张菁在多年救助被拐妇女儿童的过程中发现,地方政府各部门不但不打击拐卖,也不支持解救受害者的行动,有时甚至阻挠对受害人的救助。
“中国妇权”的团队有时要到各地方去宣传救助被拐人士的行动,但经常受到当地政府的骚扰和打压。张菁回忆说,“通常他们就是不准你做这些,要你离开,说这里不准放宣传材料,你不离开就把那些横幅撕掉。如果你要是反抗或者争辩的话,警方就把那些失踪儿童的家长统统带到派出所。”
不仅如此,从2012年开始,“中国妇权”由于资金来自国外,被中国政府认为是西方反华势力,该组织在中国的一些团队负责人先后被抓捕、判刑。他们救助被拐妇女和儿童的行动被迫转到网上,大大削弱了在地行动。
对于政府不愿、甚至打压对被拐受害者的救助,张菁分析说,从1980年代中期以后,人口拐卖已经形成规模效应,不少政府工作人员都成为了拐卖利益链的一环,“这些利益链上面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在这个利益链上的有什么人呢?有公安、有医生、民政部门、计生办,也有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还有乡政府、村委会的干部。”
她说,这些利益链上的政府工作人员为被拐受害人提供假的出生证明、上户口,甚至是上学的安排,每个环节都在扣钱,最后发展成像是连锁店一样,每个环节都已经标准化,“环环都是做好的,你拿去就好了,你交钱就行了。”
本台记者向前述那位警员求证是否存在这样的利益链,他回避了这个问题。
消失的乡绅 弱势的宗族
在政府公权力对被拐妇女和儿童的救助上麻木不仁的同时,问题的另一面是,乡村自身为什么能容忍以被拐妇女为对象的强迫婚姻?一位居住在华东某省的村民匿名向本台分析说,在铁链女事件中,作为铁链女的丈夫董某民也是受害者,“他是什么受害者?他是我们这个国家愚昧、落后和麻木的受害者。”
社媒上有不少言论把这种落后归结于部分农村根深蒂固的传统父权观念。但这位村民说,乡村对于被拐卖妇女现象的容忍体现出的是文明退化,“1949年以前,中国有个文化叫乡绅文化。那个时候,农村里面有钱人的孩子去读书了,出来以后就是乡绅,有钱有文化就叫乡绅,乡绅在治理中国这个基层,但他们恪守着中国的伦理道德。”
他认为,这种乡绅文化在1949年以后被消灭了,给乡村治理带来了一些问题,“我们现在乡村治理是靠村委会、村支部这些机构,这是党领导下的政府机构在治理,这种东西就到不了老百姓心里去。”
出生于湖南的人口学家易富贤观点与之相似,他看重的与乡绅文化关系紧密的宗族文化,“在宗族社会,婚姻是结两姓之好,是联系两大家族的纽带,不可能让一个凭空买来的、来路不明的人进入家族。”
他观察到,中国各地人口拐卖的严重程度与当地宗族文化的强盛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事实上目前人口拐卖比较严重的地方,象山东、河南这些省,他们的宗族势力是比较弱的,但家族势力比较强的,象广东、广西和湖南这些地方,人口拐卖就比较少。”
失调的性别比
治理环境逐渐弱化的乡村似乎自身也是被动的,人们更关注到这一现象背后的政策成因。
人口拐卖在中国、乃至世界古已有之。哈佛大学人类学荣休教授詹姆斯·沃森(James L. Watson)在1980年发表文章说,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人口贩卖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此类市场之一。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就是取材于民国时期社会现实的被拐妇女形象。
但在本台记者本次的采访对象中,多数认为,现在中国的人口拐卖市场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开始形成。
海外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回忆他们那一代六、七十年代在乡村当知青时,很少听到有人口拐卖的事情,“毛时代这种情况是相当少的,他把每个人都定得死死的,人走不了啊,人员没有流动性;连人都快饿死了,都没有办法到城里面去讨饭,那些女子你怎么去倒卖嘛?”
1980年代起,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增强,同时也开始严格实施计划生育政策。
人口学家易富贤认为,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导致性别比失调,是妇女拐卖的主要原因。他分析说,一胎化政策导致了选择性堕胎,由于传统上偏爱男孩,受害者往往是女性,这导致中国性别比从1980年代就不断攀升,“到2000年代的时候是100个女孩对应120个男孩。到了近期2020年,在实行二胎政策之后,性别比才下降到100比111,但这仍然高出正常的范围。”
人口学一般认为,正常的性别比是男女比例保持在100比104-107。但根据去年完成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男性比女性要多出3490万。中国第一财经网在报道中指出,这种性别比意味着,在婚育期的人群中,平均5个男性中将有一个找不到配偶。
光棍村的形成
性别比失衡还有可能促发了光棍村数量的增加。易富贤认为,光棍村的问题以前就存在,因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贫穷乡村的男子娶亲难,但人口政策导致的性别不平衡加剧了光棍村的问题,使其从个例变成普遍现象。
美国三一学院农业学荣休教授文贯中则认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人口流动也是光棍村形成的重要原因,“本来就性别比例失调,现在又有了人口自由流动,当地女子就大量外出,当地比较能干的男子也是外出,因此就留下了那种比较‘老实巴交’的男子,当然他们仍然有人所固有的那些欲望。”
凤凰周刊2019年根据媒体对光棍村的报道,绘制了一幅不完全的中国光棍村分布图,其中包括甘肃、河南、陕西、安徽、重庆、贵州、广西和海南等省市。报道强调,没有被报道出来的光棍村还有更多。
而文贯中所说的留守在光棍村里的那些“老实巴交”的男子,似乎也正是被拐妇女买家的典型形象。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助理教授熊婉茹2月24日在财新博客上发表文章,通过整理案卷中的996个拐卖妇女案例揭示出,收买被拐卖妇女的男性普遍年龄大,受教育程度低,缺乏劳动技能,经济条件差,社会地位低。
熊婉茹认为,在经济发展、人口流动以及性别比失衡等因素层层挤压之下,留在农村的贫困男性陷入了无人可娶的绝境中。
乡村的生与死及其“反抗”
熊婉茹似乎是在为这些无人可娶的农村男性叫屈。在铁链女形成的舆论风潮中,这是少有的声音。
对这些男性抱有同情的还有中国作家贾平凹。他在2016年发表了以被拐妇女为主角的小说《极花》,他在事后接受采访时说,“(拐卖)从法律角度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
但这一说法最近被网友挖出来后,引起巨大的反弹。一度有人在社媒上愤怒地驳斥贾平凹说,如果那些光棍村要用锁链来防止老婆逃跑,那就让他们断子绝孙吧。这类似的发帖在社媒上获得极高的点赞和转推率。
在这些舆论中,乡村仅仅成了评头论足的对象,正如铁链女不被村民关心一样,乡村自身的生与死也无人关心。而这似乎是中国舆论界谈到妇女拐卖时的一贯论调。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后李磊2017年在学术期刊《德州学院学报》上发表文章,为此抱不平说,在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城市对农村的结构性剥削愈演愈烈,农村强壮劳动力不断被吞噬,自然村不断在加速消亡,人们对此视而不见,仿佛这是一种抽象的存在。
他说,农村、农民无法通过正当的手段进行发声反抗,只能在日常生活之中苟延残喘, 默默承受,但绝不能断子绝孙,因为这是他们的底线。一旦剥夺触及到了这一底线,他们就只能通过不合法的暴力行为来反抗。言下之意,他把拐卖妇女看作是农村的一种不合法“反抗”。
这或许是一种文学性的表达,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对这种观点抱有同情,他告诉本台,拐卖妇女固然要打击,但农村男子的娶亲问题应该想办法帮助解决,“现在很多所谓妇女拐卖都是通过非法的婚姻中介,它是地下的,实际上做着买卖的事。所以,应该让相应的婚姻中介浮出水面,到地面上来,才好规范、管理。所以需要一定的法律,哪怕你是地方性的。”
他建议说,针对目前男多女少的现实条件,甚至可以采取一妻多夫的制度,因为人类历史上有类似的先例,“1650年,德国纽伦堡议会就通过了一个决议,就是鉴于在三十年战争中有大量的人死于战争、瘟疫和饥荒,要恢复人口,明确提出,一个男人可以娶两个妻子。”
政府的办法
政府似乎并不缺乏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手段。正在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坚决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就在上周,中国公安部也宣布,自3月1日起至12月31日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
但政府坚决的“口吻”并没有平息社媒上对铁链女事件的愤怒和关注。3月8日,国际三八妇女节,网民在微博上、微信上贴出大量铁链女的照片、图画和视频,以示提醒和警示。有网友在微信上发帖说,“我们不停地努力,因为我们知道,一旦热度没了,我们就输了。”他们对政府的能力似乎充满疑虑。
1980年代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进行过多次打击人口拐卖的专项行动,但并未能有效清除人口拐卖的现象。
前述那位警员分析说,这种运动式执法的确效果有限,“所以,我觉得应该静下心来。我当了多年警察,我常常想应该如何改进公安工作一盘棋,提高它的管理,让这种管理切合实际工作的需要。”
纽约州立大学的学者郑恬恬则在文章中指出,中国政府应该改变单纯依靠自上而下打击拐卖的行动,结合民间组织,尤其是妇女团体来应对妇女拐卖的问题。
但实际上,从2012年开始,包括“中国妇权”这样的组织,尤其是有海外背景的民间权益组织,就受到政府的严厉打压,它们在妇女儿童权益等领域的作用已大为削弱。张菁告诉本台,“中国妇权”大约有五年时间是做援救的在地行动,但总共只营救了28个妇女儿童,“这个(营救)比例确实非常非常低,让人确实感觉很心酸,因为有那么大的群体。”
从这次铁链女事件可以看到,起推动作用的并没有民间组织的角色,而主要是在社媒平台表达的民意。
结语:春天最美好的声音
借铁链女事件喷发出的汹涌民意似乎成了被拐妇女在这个春天可以听到的最美好的声音。对揭露铁链女真相起到关键作用的前记者邓飞,3月5日在他的微信朋友圈转帖了河南省要求全面排查农村“已婚智力、精神残疾妇女”情况的通知,他附上一句短评,“改变正在发生。”
但对于很多外界甚至不知道身在何处的被拐妇女来说,她们的春天将在何时到来,人们仍在期待。
( 本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jpeg)
.jpeg)
.png)
.png)
.jpe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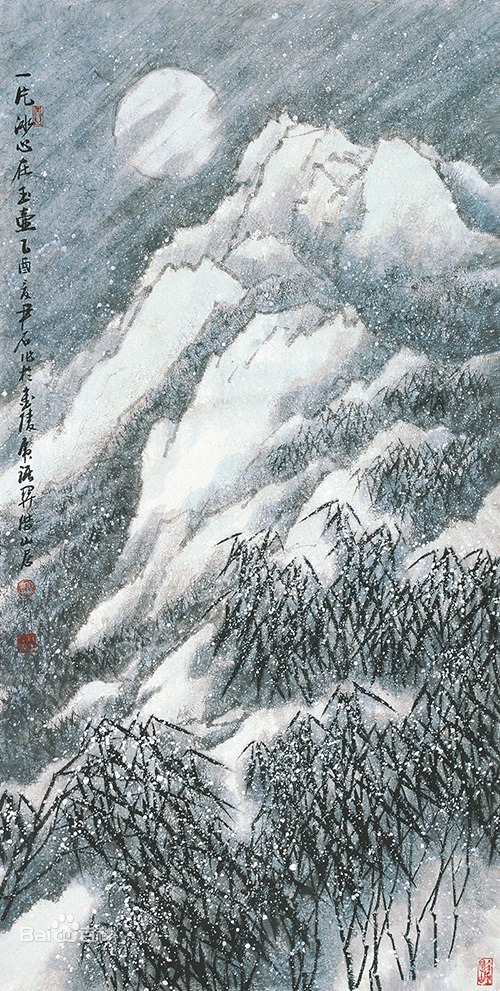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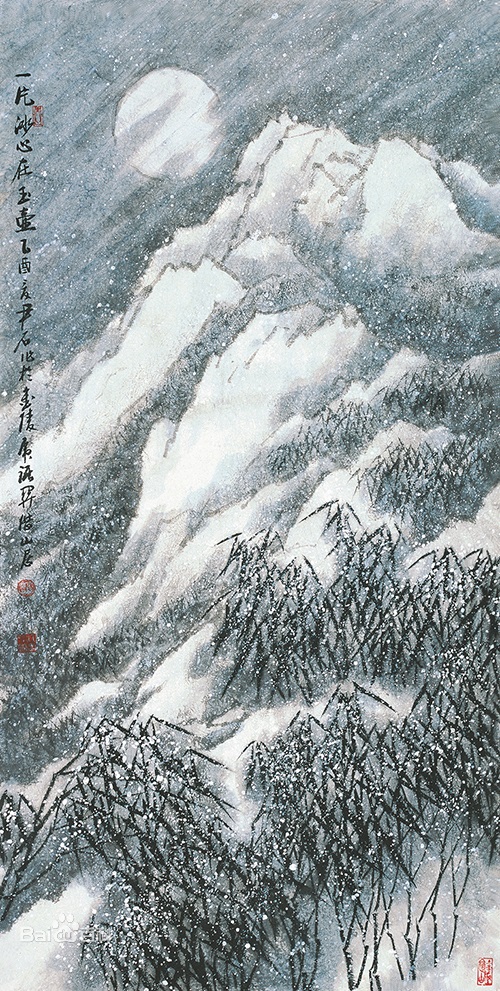


-1.jpg)
.png)